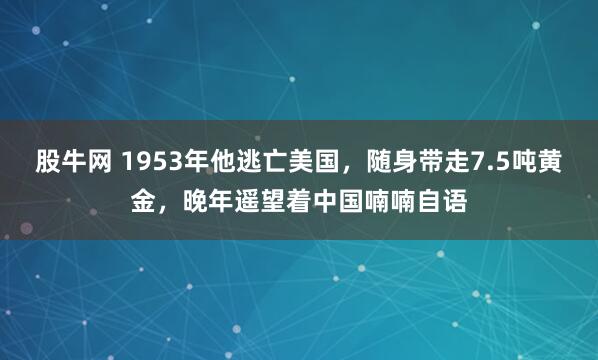
1953年夏天,香港启德机场闷热潮湿股牛网,海风裹着汽油味钻进鼻腔。
跑道尽头,一架银灰色的道格拉斯包机低声轰鸣,螺旋桨一圈圈转着。
机舱里,几排木箱整齐码好,用粗厚的帆布裹着,角落处露出锈迹斑斑的铁扣,搬运工喘着粗气,小心地把最后两只箱子抬上机。
这些箱子看似平平无奇,实际上,每一箱都沉甸甸到极限,里面装着的是黄金,足足7.5吨。金条、金叶子、金元宝,还有镶嵌着红蓝宝石的首饰,被麻袋分隔装好,像等着过海的货物,却是一个人半生的积攒与整个省份的血汗。
坐在第一排的男人,西装笔挺,手边的皮包里放着美国入境文件和几本银行存折。
他沉默不语,偶尔抬眼看向窗外。
那是马鸿逵,曾经的宁夏省主席,权倾一方的“土皇帝”,也是让蒋介石又用又防的“西北四马”之一。

这趟航班的目的地,是美国洛杉矶。
对外的理由,是陪四姨太刘慕侠赴美治病,真正的原因,只有他心里清楚这一次走,可能就是永不回头。

十几年前的宁夏,表面上是边陲小省,实则是马鸿逵的独立王国。
省政府大楼里,他的办公室铺着进口地毯,墙上并列挂着蒋介石的肖像和他本人的照片。
每天清晨,卫兵列队站岗,侍从送来当天的公文、情报和各县上缴的银元。
他掌握着宁夏的军政、财政大权,修路、征税、兴学,都是他说了算。
百姓见他股牛网,低头鞠躬,不敢直视,军队士兵则以能在马鸿逵麾下服役为荣,哪怕是当个传令兵,也算是进入了核心圈子。
表面上,他爱好教育,奖学金资助了不少寒门学子,还修建公园、电影院;可暗地里,他大印“金圆券”,逼老百姓用银元、金饰换取,兑换率极不公平。

很多人一夜之间失去全部家底,金子进了他的库房,换回来的纸币却日渐贬值,沦为废纸。
这些金银珠宝,成了后来逃亡的“底气”。
马鸿逵之所以能在宁夏呼风唤雨,并非偶然。
他的祖父马千龄,在清末回民起义中劝降马占鳌,既保住了马家的兵权,也赢得了左宗棠的信任,被称为“良回”。
父亲马福祥更是老于世故,先后投靠袁世凯、冯玉祥,最终在蒋介石麾下站稳脚跟。
1892年,马鸿逵出生在甘肃临夏。
少年时,他进了甘肃陆军学堂,学射击、骑马、战术,也学会了军政的潜规则。

年轻时,他曾因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而被捕,靠家族运作才保住性命。
从那以后,他学会了收敛锋芒,把热血换成耐心和算计。

抗战胜利后,国共内战全面爆发。
马鸿逵表面上追随蒋介石,但在实际战场上动作迟缓,还与堂兄马鸿宾争夺兵权。
蒋介石开始削弱他的势力股牛网,把嫡系调离宁夏。
1949年,兰州战役爆发,马家军在解放军的攻势下迅速崩溃,溃兵四散。
马鸿逵弃城而逃,先去了重庆,又被安排到台湾。
然而到了台湾,他发现自己成了闲人,没有兵权,官职虚悬,随时可能被清算。
在台湾的日子,他越来越感到危机逼近。
他明白,对蒋介石来说,自己早已失去利用价值,留在身边只是个麻烦。
唯一的活路,就是带着金子走远。

他挑了个理由,就说四姨太刘慕侠“急需赴美治病”。
黄金分批运到香港,用货船、卡车伪装运输。为掩人耳目,他还在台湾刻意出席一些公开活动,制造安分的假象。
1953年初,一切准备就绪。
他和家人先飞到香港,住进九龙的豪华酒店,几天后登上了那架包机。
飞机冲上云霄时,马鸿逵没有回头,他知道,等蒋介石反应过来,自己早已在大洋彼岸。

初到洛杉矶,马鸿逵住进郊外的豪宅,买下大片牧场,养马、养狗,出行都是凯迪拉克和林肯。
他喜欢举办宴会,请当地华人和旧识赴宴,席间谈论宁夏的风沙、马家军的往事,仿佛还是那个权势滔天的省主席。
洛杉矶的阳光、牧场的青草味,让他短暂地忘记了失去权力的落差。
可这样的生活,很快露出另一面,奢华意味着高额开销,投资失误让财富不断缩水。
不到十年,那7.5吨黄金已经消耗殆尽。

牧场卖了,豪宅换了主人,凯迪拉克也不见踪影。
家里的儿女为剩下的财产争得不可开交,姨太太之间冷嘲热讽。
往日的“宁夏王”,此刻只能靠变卖家当维持体面。
他开始搬家,生活一缩再缩,身边的随从和仆役一个个离开。
在异国的华人圈,他的名字慢慢被淡忘。
六十年代末,马鸿逵病重,常年在医院。
他喜欢让护士推着轮椅到花园尽头,那里可以看到一片空旷的天空。
他总是盯着东方出神,有时会低声说:“我是中国人,死后要葬在中国的土地上……”
1970年1月14日,他在洛杉矶去世,享年78岁。
遗体被送到台湾,安葬在台北回教墓地,离宁夏,依旧万里之遥。
那7.5吨黄金,换来几年虚假的安稳,却换不回家乡的一抔黄土。
思考资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鑫宝 成都蓉城球迷会宣布停止应援两场比赛,以此向俱乐部抗议
- 下一篇:没有了







